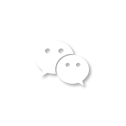那天,她坐在会议室内,给自己的先生、弟弟和儿子传了一条内容相同的短信,告诉他们:我现在正坐在会议室中跟新同事开视频会议,屏幕上的是美国合伙人,他们都讲英文,话题也都是我陌生的投资案。
不久之后,他们分别回了她一条短信。儿子传回的短信是:“没什么妈妈,即使是懂英文熟悉投资案的人也会觉得这样的形式挺无聊的,慢慢你就会适应了”;学英文的弟弟则说:“没有语言工具就更难,还得想个办法把此事解决一下,不然会影响工作。你有空可以给我电话,聊一下具体解决方案”;先生的短信最意味深长:“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稍安毋躁,顺其自然”。
“你看,我很会沟通吧,我一个短消息发给三个人。”第二天,在她位于上海淮海中路上的办公室内,这位昔日上海最知名的企业家在接受《经济观察报》的访问时开玩笑说。这也是她从光明乳业董事长职务上解甲后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长时间访问。
但是对于这位前光明乳业董事长而言,事情绝非如此轻松。她坦承自己感到压力,“我真的是如坐针毡,老外的话我很多都没听懂。我该怎么办?”
她对自己的新同事说,以后开会你们一定要给我议程,投资案事先给我看;同时,她开始重新温习英文。
说这些话时,王佳芬仍然是满面笑容。当将近57岁的王佳芬决意开始一段新的征程时,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她,在她已经调整完毕之后,妨碍她的信心,影响她的心情。她仍然保持着之前数年间出现在媒体上的形象,短发整洁,套装清爽,讲话时不自觉要提高嗓门,语速快于常人,笑容开朗,激情四溢。她甚至说自己还没有感觉到年龄带给人的压力。她仍然每天步行数十分钟,保有长期工作的体力和解决问题需要的意志力,以及对新的工作环境的适应力。
上班的第一天,作为新加入的合伙人,她开始挨个办公室地去和纪源资本的各个合伙人聊天。“我这三天好忙啊。我一有时间就跟大家沟通。我觉得沟通太重要了。”她说。
她打开信箱,信箱里是来自全球的新同事的欢迎信。客套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理解这家公司。我跟这边的很多合伙人做了交流,问他们怎么理解资本,我们公司要做什么,我们怎么去想这些问题;然后他们在谈的一些项目,我开始介入”。她的一个同事说,当一家公司的高层看到王佳芬代表纪源资本出来和他们谈判投资事宜时,“非常震惊”。在同记者会面的当天早上,王佳芬就出发去谈了一个项目,一谈就是三个小时。“谈的结果会决定我们接下来是做还是不做。我感觉很兴奋,觉得自己很有责任,也有压力。这很有意思”,她说。
还有一些更细微的事情需要她来适应,“比如之前我在光明乳业是很多秘书围着我转,现在很多事情我要自己处理;还有,之前一直是使用司机,现在,我要自己学开车”。
二
40岁才开始自己乳业女王生涯的王佳芬,并不畏惧任何改变,这从她的过往生涯中就可看出。在她于1992年的大年初六接到上海市农场局局长罗大明的电话,邀请王佳芬到家中作客,然后劝她出任上海市牛奶公司总经理之前,王佳芬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名成功的国有农场经营者。她曾经是学大寨的狂热分子,但她也是一位实干家和头脑灵活的农场长。她领导的农场业绩让她在整个上海市的农场局系统中出类拔萃。这也是为何罗大明会考虑让王佳芬接任上海牛奶公司总经理的原因。这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即使王佳芬选择继续留在政府系统中,她也会沿着既定的道路向上升迁。
真正的意外是,选择进入公司成为一名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后,她仍然能够取得成功。尤其考虑到她进入牛奶公司之后没有多久,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开始进行改革,而改革毋庸讳言的原因是,它们中的大部分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大规模的溃败。
在王佳芬的领导之下,上海市牛奶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光明乳业,不但活了下来,而且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成为翘楚。这家199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是第一家尝试占领全国市场的乳业公司。之前,国内的乳业公司受限于奶源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全部是区域性的牛奶公司。而王佳芬提出的“用全国资源做全国市场”则让光明树敌无数。她的竞争对手不仅仅包括各地的乳业公司,甚至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在她的竞争对手看来,王佳芬是徒劳地想要“让全国一片光明”。不过,这句嘲讽王佳芬和光明的话,后来却成为对她和她的公司的赞扬。
即使已经过了鼎盛时期,到目前为止,光明乳业仍然保持着在新鲜乳制品行业的绝对领先地位:新鲜牛奶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市场份额达43%;新鲜酸奶市场占有率33%,仍然是全国第一;奶酪制品市场份额45%,还是全国第一。
“很早的时候,因为上海没有奶源,对光明而言肯定是制约因素。我们当时就说光明可以用全国的资源来做全国市场,可以用世界的资源来做中国市场,这点上我觉得自己是开放的,对全球经济的发展我是拥抱的,一定要把别人的好东西拿过来,我今天还是这么想。当时我就以这样一种很开放的心态去发展光明的全国奶源。上海没有奶源,但黑龙江有,你完全可以把工厂建到那边去,谁也没有说你不能做。我觉得只要自己不束缚自己,那么前途就无限光明。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束缚自己。我们当时开人代会的时候,大家说国有企业改革不行,提了一大堆的意见,我那时候就不提什么意见。我觉得,谁都没跟你说不能做,只是你自己思想上告诉你不能做,你做了又会怎样。他们说你做了就要查你,但你不拿到自己口袋里怕别人干什么?因为我无私,我不束缚自己,所以我就什么都不怕。”王佳芬在回忆最初光明改革和走向全国时的心态时说。
在王佳芬的十五年光明生涯中,她数次扮演了“吃螃蟹的人”。包括同外资的接触与合作,以及同麦肯锡的合作。这些合作并不总是被人褒奖。但是王佳芬却以无畏和开放的心态去进行最初的尝试。“我并没有把光明看成是一家国有企业,我把它看成是一个公众公司。而我则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她说。
她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光明乳业,作为一家从产权上来讲属于国有的公司,在缺乏对管理层的激励和改革的直接动力的条件下,成为少有的在竞争性行业中真正具备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而大多数国有企业不是一败涂地,就是凭借着身处资源性行业,或者享有在本行业内的垄断性优势而生存。淘宝网女装夏装新款瘦腿祛痘产品哪种好洗面胸部小怎么办护肤燕麦片减肥效果好
三
任何人要想在我们所刚刚经历的特殊时段中扮演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都有可能。我们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精英分子。他们在各个历史阶段扮演了弄潮儿的角色,从广场上慷慨激昂的领导者,到集体农庄、工厂和政府机关中尽心尽意的理想主义者,再到市场中春风得意的竞争胜出者。但真正困难的是一个人在各个时段都能够显得出类拔萃,能够快速地适应变化的时代——不但适应,而且理解,进而从理解演变为积极参与和略胜一筹。
对于王佳芬而言,她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这样的多时段成功者。她将之归功为自己的开放性思维。
“我一直在用比较开放的心态思考,而且我有自我,或者说,不是一点自我都没有”,她说。从早期知识青年中的积极分子,到后来农业学大寨的先进表现者,再到一个成功的政府工作人员,继而是一名国有企业和接下来上市公司的领导者,然后到今天进入投资领域,王佳芬似乎从没有停止过改变自己,以让自身来适应动荡的时代和迅速变迁的大环境。
“一旦党的方针政策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马上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王佳芬回忆说。1983年王佳芬和众多来自上海各个政府部门和公司的被选中者在党校学习邓小平理论。他们都是上一时段的精英分子。“我钻在图书馆里面去研究商品经济的理论是什么,看完了以后我发言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点是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这跟我们共产党讲的集体主义、一心为公是两码事,那么我们共产党要推出这套政策,势必跟我们以前所讲的很多东西不一样,我说我们必须准备按照这样的规律来建立市场经济的秩序。当时党校里面有人跟我辩论,说你这个东西不对,党的原则永远是这样这样的。我说不是的,你如果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这套理论。”
她迅速地调整过来,她说自己学习了很多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而且“特别赞同”,正如她之前也曾经相信和赞同计划下社会理想一样,“过去是政府配置资源,市场经济是市场自由配置资源,我认这个理儿,我就按这条规律去做。然后我再去研究好的国际公司的经营方法,它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有什么样的理念。”
同她的开放心态和适应能力相匹配的,是她的学习能力。这在她十五年光明乳业生涯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仅是她个人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由之而来的学习欲望,她还用个人的学习欲望去驱动整个公司的学习。她说只要允许,自己总是乐于倾听任何一个人的言谈,哪怕对方有些喋喋不休。这让光明的一些年轻人深感荣幸。
“开始的时候光明在乳品上的技术也不是特别的强。但如果你很用心的话你都可以学到,全世界都是开放的。学习的手段也可以有很多。”王佳芬和光明从他们每一个合作者身上都有收获。这种学习能力让人震惊。王佳芬和达能之间的不快的开始,正是达能在技术上的吝啬。达能不愿意再在合资企业生产新产品。原因是,他们惧怕光明学习到这些技术之后,通过价格战击败达能。当达能被迫将上海的工厂卖给光明时,达能的中国工作人员对法国总部说:“不是因为我们不行,只是因为‘共军太狡猾’,王佳芬的学习能力太强了”。除此之外,她还推动光明的员工到国外学习育种技术,向合作对象学习运营方式等等。对于她个人而言,她也善于通过和不同的人的交流来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王佳芬的一个朋友评价说,“王总你真聪明,你会在不同的时候找不同的人做你的朋友。”
一次,几个乳业公司的领导者在进行交流时,牛根生说:“蒙牛拥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采用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企业制度。”这种产权上的优势,正是蒙牛能够借助资本力量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王佳芬当时反驳说,她并没有感觉到光明对自己的约束。但后来,即使是王佳芬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过去十五年对她和光明最大的制约之一。
但是王佳芬一直认为自己能够成功地驾驭这种微妙关系,在两种规则之间游刃有余:一方面是国有产权和其中残余的行事规则,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竞争激烈充分市场化的行业。“我一直认为你们是对的,你们的游戏规则也是对的。只是我需要到另外一个体系中生存……我只是在我的游戏规则中做我自己的事情,我永远不说别人不好。”
她在处理这种微妙关系时表现出令人惊叹的情商,她在自己的双重身份间来回穿梭,她是一个上市公司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一个国有企业系统的一员。“我每次发言,别人都会对我印象很深,因为我略微有一点与众不同,但我也不会把领导说得反感。那个时候我们开人大,第一次开预备会,就让每个人说一说,我说完之后,人大会马上就让我发言,后来一直叫我发言……所以我很容易成为发言的专业户。”
“我进会场要看一看我今天是什么位置,今天要干什么,然后马上把自己调整好,决定自己要说什么。我同样一个观点会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来,但是我一定要完整表达出我的思想。所以光明乳业的同事就说我换频道的能力很强……我尽量从他们的角度,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听得进去的语言去说,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能力,因为你一定要为你的目的服务。他们很喜欢叫我发言。”
王佳芬的这种长袖善舞,让她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乳业市场上为光明博得一席之地。不过,尽管她承认自己曾经致力于解决光明乳业的制度和产权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没有斩获。与此同时,外界认为光明开始落后于异军突起的蒙牛和伊利,后两家乳业公司都先后解决了困扰王佳芬已久的制度制约因素。
当然,可能包括王佳芬在内,光明乳业的一些旧将仍然坚持认为,光明乳业虽然暂时在销售额上落后,但却押中了未来,而乳业的未来就是两个字:新鲜。只是王佳芬并未能亲眼目睹自己对新鲜的坚持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是未来的一路领先,还是错失常温之后元气大伤。她已经踏上了新的征程。老兵不死,可也并未凋零。一个在中国短暂公司史中多次领时代之先的企业家,曾被人冠以铁娘子和女王的称号,如今要在她57岁时重新开始杀入商业战争的前线。只是这次,她是作为一家投资基金的合伙人。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片商业的新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