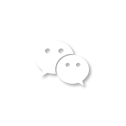一向备受国人瞩目的乳业行业最近热闹非凡。
先是蒙牛乳业[微博]以124.6亿港元收购广东乳企雅士利,这是中国乳业近年最大的一笔收购;随后出现伊利竞购飞鹤乳业和完达山乳业的传闻;与内蒙古乳业双雄不同,上海的光明乳业(13.50,0.01,0.07%)则将触角直接伸向海外:其发公告称,之前收购的新西兰乳企新莱特乳业(Synlait Milk)拟在新西兰证交所主板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IPO)。
在这一轮乳业的全行业整合与变局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曰做大,工信部有言,要整合出10个左右年产20亿吨以上量级的乳业大鳄来;二曰国际化,以上提到的几个整合参与者,都和同一个国家有关——新西兰。伊利和雅士利都在新西兰设有工厂,其中雅士利的工厂预计2014年下半年投产,只是那时应该已经改姓蒙牛。
这一轮折腾,是否能给国人折腾出一杯放心的牛奶?
大而不倒,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这已成为中国乳业欲说还羞的真理。作为上市公司,从资本市场看,这些行业龙头都是“成功者”。但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人对国产奶粉的信心正在降至冰点,随便去一个一二线城市的大型超市转一圈,看看货架上那一排排售价不菲的洋奶粉,就可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这些龙头企业都选择了新西兰来帮自己做大、国际化,那么不妨转换下视角,来看一看,新西兰这个人口不足500万的太平洋岛国,何以成为全球最负盛名的乳制品制造国,新西兰奶粉为何成为中国父母争相求人代购的产品,最重要的是,是不是牵手新西兰,就真的可以灵验到让中国乳业走出困境?
新西兰的首都是惠灵顿,但是最大的城市是奥克兰,这座城市据说现在有10%的人口是华人,以至于机场的工作人员看到黄皮肤的人就会说句生硬的“你好”,向你致意。但是,最近,奥克兰却上演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反华风波。
候任奥克兰机场董事会主席Henry van der Heyden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要小心中国人。当然,这样的演讲肯定“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特别是在新西兰政府正在靠源源不断地把乳制品出口到中国换取大量外汇的时候,最后,这位Heyden先生被迫道歉。
Heyden先生的上一份工作是恒天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恒天然是全球最大的乳制品加工企业之一,如果说乳业是新西兰的骄傲和经济支柱,那么恒天然就是新西兰乳业的金字招牌。Heyden先生在任期间,恒天然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之一三鹿乳业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虽然恒天然中国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最终通过外交努力将此事汇报给了中国政府,并直接导致了三鹿乳业的垮台,但事情传到新西兰国内,新西兰民众听到有婴儿因毒奶粉而丧命,依然对恒天然不依不饶,认为其应承担对中方合作伙伴监管不力的责任。
这是一个对商业道德极其敬畏的国家,也是笔者访问新西兰后最深刻的感受。当然,人口稀少是一个原因。因为人口少,很多地方都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在这种熟人社会中,道德的威慑力远大于法律因素。
但是许多国内的朋友对此颇为不屑,“谈道德也太虚无了”,他们认为,即使道德感是新西兰乳业成功的一个因素,也不应该是最主要的因素。我也相信人性本恶,一定存在着某些制度安排,可以让人们藏起他们恶的狐狸尾巴,不往牛奶里面加其他东西。
对比近年来中国乳业发展的趋势,可以发现两国区别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第二,规模化养殖质量高是否就意味着大牧场,散户是否应该退出市场?
2009年中粮携厚朴入股蒙牛,当时一位投资人感叹道,这样一来四大乳企全部“收归国有”了。自此之后,国家调控之力愈发明显,今年蒙牛增持现代牧业股份为其最大股东,可视为国企(中粮)向乳业上游渗透的开始。而工信部发布的《提高乳粉水平提振社会消费信心行动方案》,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鼓励行业兼并。但在行业前四都是国企背景下,这显然是进一步国进民退的信号。
另一方面,自三聚氰胺事件以来,中国乳业一直在反思,一直在学习国际经验,学习的结果就是消灭散户,就像土改时消灭小农、全国学大寨一样,直到现在,你如果去翻一些报道三聚氰胺的媒体报道,也会说散户是乳业之乱的根源,等等。
三聚氰胺事件时去过一线的记者都应记得,当时反馈的情况是问题出在奶站,最后被抓判刑的也是奶站的人,这都有法律文书可查,但是数年之后,罪责已经笼统地被“散户”所承担。
但是在新西兰,政府鼓励公开透明高度市场化的产业环境,对于政府,提醒自己不做什么似乎更为重要,这包括:不提供出口退税,不指定配额,不提供农民补贴。
而且,细细拆解新西兰的乳业产业结构,我发现由散户主宰的家庭农场仍旧是整个乳业产业结构的细胞。虽然新西兰有恒天然这样每年出产数百亿吨乳制品的加工制造企业,但是恒天然本质上也是一个奶农持股的“联合体”,是“奶农的联合国[微博]”。
据统计,新西兰目前约有11600个奶牛场,平均每个农场占地约131公顷,拥有366头奶牛。这与国内动辄数千头牛的大牧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这一发现并不是新奇,国内早有论者对此进行论述。然而,不管怎样,中国乳业近年的反思结果,似乎只有“大跃进”一途,推行规模化养殖,所谓乳企要控制奶源,结果就是大家比着建大牧场,甚至出现了所谓现代牧业模式,把上万头牛集中在一起养殖,声称这是借鉴吸收国外的工业化养殖经验、科学养殖,可以完全可以规避环保与疫病两大风险。
我参观过国内的大牧场,确实很壮观。参观牛棚时,我们从中间走过,所有的牛都在两侧的围栏里,那感觉好像是领导人在检阅仪仗队。但是在新西兰,这样的参观机会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的牛都是顶着蓝天白云在一大片绿草地上散步,或坐或卧,只有会赶牛的放牛娃才能下“场地”,如果你非要到牧场上去“零距离”接触,那么小心被牛踩到!
如果看惯了国内的现代化的工业化养殖,你会觉得新西兰的养殖模式“很原始”,居然还在放牧。但是,在新西兰,连小孩也会告诉你,如果你想让牛奶质量好,除了吃的好,住的好,别生病,牛的心情好也很重要,这是属于牛的福祉,或者说动物福利。
有人肯定会说,这是国情不同,新西兰地广人稀可以放牧,中国怎么可能。那好吧,我们换个国家,说说荷兰。荷兰、新西兰和美国是世界著名的三大乳都。荷兰是全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按说这里应该盛行工业化养殖吧?错,荷兰也是家庭牧场模式,每个家庭牧场最多只养50-70头牛。
在新西兰由于牧场是家族所有,所以这些世代养牛为生的人们会把牧场看做可以继承的私有财产,格外珍惜自己的声誉,并且,农民都有熟练的养殖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包括恒天然在内的新西兰三大乳品合作企业要求牧场主购买合作企业的股份。合作企业保持股份价格标准,牧场主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与牛奶供应量挂钩。
在当地人看来,与工业化养殖的所谓高效率相比,中小规模的放牧养殖才是真正经济节约的养殖方式,与大牧场模式需要投入大笔资金去规避环保与疫病风险不同,理论上讲,放牧养殖的最大风险是来自恶劣天气和极端气候的影响。但因新西兰地理气候得天独厚,才得以成为乳业大国。
小规模养殖模式的另外一“弊端”是,由于受土地等条件限制,自然增长缓慢,融资也比较困难,进而又影响到牧场的扩张速度。但有研究人士认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蒙牛伊利模式在新西兰才没有生存空间,即牛奶公司在奶源有限的情况,仍旧可以靠营销把产品卖到全国。新西兰的模式其实是回归了乳业的根本,本地奶源本地加工,本地人喝,这就是最好的牛奶。
事实上,中国并非没有此类模式的受益者。在近年的乳企质量风波中,黑龙江的乳业企业很少榜上有名。业内流传的说法是,黑龙江“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当年蒙牛、伊利的员工开车去全国抢奶源时,唯独进不来黑龙江,几乎是被凶悍的东北人用棍子“打”了出来。黑龙江乳业因此保持了“本地牛奶本地产本地销”的模式,才能独善其身。
不过,在这一轮的乳业整合大戏中,飞鹤乳业和完达山乳业都在被收购名单上,前途未卜。